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个人真的存在吗?(2)
在廖平之后,胡适从思想史方面入手,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,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。在他看来,屈原是“一个理想的忠臣”,“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,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”。胡适认为,今天“儒教化”的屈原及《楚辞》的始作俑者是“汉朝的老学究”,他们把当时盛行的“‘君臣大义’读到《楚辞》里去,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……”。屈原故事是“宣帝时人”补《史记》,“七拼八凑”“塞进《史记》”的。此外,胡适还判断《楚辞》前25篇,只有一部分“也许”为屈原所作。④
还有学者认为,《离骚》真正作者是汉朝人刘安或者贾谊
“屈原否定论”还有很多其他代表性观点,比如,有学者认为,《离骚》原作者为淮南王刘安,其谋反自杀后,著作权被刘向、刘歆父子给了“屈原”;有学者认为,屈原是贾谊伪造的人物,意在抒写自己的“冤屈”;还有学者认为,《离骚》表达的不是屈原或其他特定人物的个人情感,而是“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,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”;等等。⑤
倘承认屈原存在,其身份究竟是弄臣、楚巫还是贵族,仍存争议
孙次舟称屈原是“富有娘们儿气息的文人”,和楚怀王有“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”
有关屈原身份,最著名的事件,是1944年闻一多、孙次舟之争。孙次舟是“古史辨派”创始人顾颉刚的学生,时任华西大学教授,他在一次演讲中,称屈原是楚怀王的“弄臣”,因为和“令尹子兰”争宠失败,才投江自杀的。之后,他又连续发表两篇文章,详细阐释自己的观点,称屈原虽然“天质忠良”,但也只是一个“富有娘们儿气息的文人”。《离骚》中很多诗句,如“初既与余成言兮,后悔遁而有他”,像是“男女情人相责”;“与既不难夫离别兮,伤灵修之数化”,则是“眷恋旧情,依依不舍”,指屈原和楚怀王有一种“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”——屈原其实是怀王的男宠,他们是恋人关系。⑥
孙次舟为了增加自己论证的说服力,特意拉出当时研究《楚辞》的名家闻一多做自己的“盟友”,他引用李长之信中的话,“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,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”,并谓“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,定胜拙文远甚”。
闻一多承认屈原确实是“文学弄臣”,但不妨碍他是一位“人民的诗人”
经朱自清转寄,闻一多看到了孙次舟的两篇文章,并写下《屈原问题》一文。闻一多肯定“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,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”,但“屈原是个文学弄臣,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”。在闻一多看来,屈原是“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,变成了人”,而非孙次舟想象的那样,是“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,变了奴隶”,堕落为弄臣。
1945年,闻一多更进一步,写下《人民的诗人——屈原》,推测和楚王同姓的屈原,“从封建贵族阶级,早被打落下来,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”,因此他“依然和人民一样,是在王公们脚下被残踏着的一个”。《离骚》采用“人民的艺术形式”,内容上“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”,唤醒了楚国人的“反抗情绪”。⑦
由于楚辞中有很多和占卜、巫术有关的内容,屈原也很可能是一位“灵巫”
有关屈原身份,另一个重要猜测是“楚巫说”(“信巫鬼,重淫祀”“好祭祀,用史巫”是楚国一直以来的传统)。其代表观点有多种,主要称屈原是“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”;或者更详细论证,“屈原本是一名特出的宗教优伶,一名能歌善舞的巫官”“屈原生于楚国的一个巫官世家,他一家人以巫为业,不仅屈原是巫”,其父“伯庸很可能是楚国的大名鼎鼎的灵巫”;甚至屈原的死,也被看作是“巫的升华”。⑧
从文献来看,能旁证屈原和楚巫关系的材料颇多。首先,屈原爱穿“奇服”,诗中“披明月兮佩宝璐”“佩缤纷其繁饰兮,芳菲菲其弥彰”等花草服饰,说的可能都是巫服;其次,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自称名“正则”,字“灵均”,经考证,这两个名字都是通过占卜所得“嘉名”,具有“宗教职业味道”;第三,署名“屈原”的作品中,大量出现“彭咸”之名,这应该是“巫彭”“巫咸”的简称,代表某些大巫,是屈原的人生榜样。
相关文章:
相关推荐: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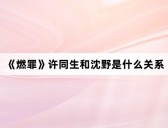 《燃罪》许同生和沈野是什么关系
《燃罪》许同生和沈野是什么关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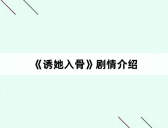 《诱她入骨》剧情介绍
《诱她入骨》剧情介绍
 《股掌之上》剧情介绍
《股掌之上》剧情介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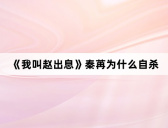 《我叫赵出息》秦苒为什么自杀
《我叫赵出息》秦苒为什么自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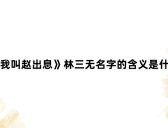 《我叫赵出息》林三无名字的含义是什么
《我叫赵出息》林三无名字的含义是什么









